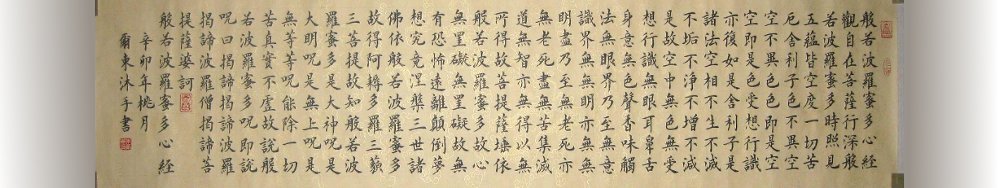評《大正新修大藏經》之三
作者:方廣錩 發佈日期:1996年2月
接:評《大正新修大藏經》之二
三、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問題
敦煌文獻絕大多數為佛教文獻,從時代上講,其年代最早者可達西元四、五世紀,晚者則為西元十一世紀,時間跨度達600餘年。從抄寫者講,這些寫卷有的出自宮廷楷書手之手,有的出自敦煌當地寫經生之手,有的出自其他諸色僧俗人等之手,水準參差不齊。從內容上講,大多數為歷代大藏經已經收入的典籍,也有相當數量為歷代大藏經不收或漏收的典籍,還有許多儀軌、雜文乃至錯抄的廢紙與習字的塗鴉,可謂雜亂無序。由於年代長久,不同年代寫經之字體因古今演化而異;由於抄寫者眾多,寫經品質參差不齊,錯漏增衍實為常事;由於內容歧雜,必須對它們進行鑒別,然後才可以利用。加之它們本來就是一批被人廢棄的古文獻[0],所存寫經不但頗多殘頭斷尾,而且魯魚亥豕之處,在所難免;文意漏斷之處,亦為常見。此外,有相當一批文獻是在敦煌本地產生的,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諸如敦煌俗字、河西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交涉互用等等。凡此種種,更增加了閱讀與利用的難度。不過,在敦煌文獻中,同一種文獻經常保存有多個抄本殘卷,如果把這些殘卷的內容綴接、拼湊起來,再加以認真校勘,則往往可將殘缺不全、文字錯訛的文獻拼湊完整,校為定本。由於有些文獻尚有傳世本,故校為定本時必須與傳世本對勘。凡此種種,結合傳世文獻,對敦煌文獻,特別是對歷代大藏經中沒有收入的諸種文獻進行鑒定、定名、綴接、釋讀、校勘、錄文,成為對這些敦煌文獻進行研究的前提與先決條件。
《大正藏》編纂時,敦煌文獻已經被發現,所以,收入敦煌文獻,便成為編纂《大正藏》的四條原則之一。《大正藏》共計整理、發表敦煌文獻約200種,達250多萬字。這些文獻主要集中收錄在第八十五卷中,約有180多種;其餘十餘種則散在其他各卷。把敦煌文獻如此集中地彙聚在一起,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它既大大便利研究者的使用,也使研究者對敦煌文獻的價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與瞭解。
《大正藏》的上述整理工作也存在若干不足之處,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所利用敦煌文獻的覆蓋面有限。
《大正藏》所收入的敦煌文獻絕大部分依據矢吹慶輝從英國倫敦考察所得照片錄文。少量文獻依據赤松秀景、山田龍城在法國巴黎調查所得錄文,個別文獻依據中國出版的北京圖書館敦煌文獻錄文,或依據大穀探險隊所得敦煌文獻乃至中村不折等私人所藏敦煌文獻錄文。由於所依據的原始資料有限,所以收入的敦煌文獻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僅收入200種左右,與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大量未入藏佛教典籍相比,僅占一小部分。由於依據的原始資料有限,故出現一些問題。如《首羅比丘經》、《大通方廣經》、《天公經》、《天請問經疏》等不少文獻,矢吹所見的寫卷均為殘本,而敦煌文獻中尚保存有這些文獻的其他寫卷,可以據以補足;又如《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矢吹所依據的寫卷有大段缺漏,而敦煌文獻中該文獻尚存有抄寫品質更好的其他寫卷,更適宜用作底本。
第二,有些典籍不應收而收入,有些應收入而未收。
如第2913號《七女觀經》,系歷代大藏經已經收入之小乘佛教經典,此次誤作疑偽經收入;第2770號《維摩經疏》,實際為隋慧遠撰《維摩義記》,已收入《大正藏》第三十八卷。有些典籍因鑒定有誤而重複收入,如第2741號《金剛般若經疏》實際是第2733號《禦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的另一個抄本。有的如第2775號《維摩疏釋前小序抄》與第2776號《釋肇序》本為一卷,卻分為兩種文獻錄文,且《釋肇序》的正確名稱應為《釋肇序抄義》。有些典籍如《父母恩重經》、《佛母經》、《新菩薩經》等有多種異本,但《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則收入其中一種。
第三,錄文也有可議之處。
如《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原卷有一段文字本來是書手錯抄後廢棄的,故特意在前後用“┓”與“┗”加以標誌,但錄文者不察,把這段文字錄入正文,以致文意扡格。又如《大乘二十二問》最後有一段話介紹佛教部派的分佈,稱“其法藏部本出西方,西方不行,東夏廣闡。”但《大正藏》錄文時漏“西方”兩字,誤作“其法藏部本出西方不行東夏廣闡。”[1]
當然,《大正藏》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出現這些問題,主要是由於客觀條件有限所致,我們不能苛責前賢。
四、校勘問題
校勘問題可以分為幾個方面,下面分別談談。
第一,重出問題
有些經本,明明已經收入,卻由於編纂者疏忽而再次重出。如《金剛經》傳統有六個譯本,但《思溪藏》在收入《金剛經》時,錯把陳真諦本當作是元魏菩提流支本,而把真正的陳真諦本漏掉了。《大正藏》依據《高麗藏》收入菩提流支本後,發現《思溪藏》的菩提流支本(如前所述,實為陳真諦本)與《高麗藏》本不同,便把它當作菩提流支本的另一種抄傳形式(術語稱“別本”)再次收入。這樣,《大正藏》所收的《金剛經》便變成七種。其實,元代的《普甯藏》就已經發現並糾正了《思溪藏》的這一錯誤,並特意撰寫了一段說明,附於經後。《大正藏》也以《普甯藏》作為主要參校本,卻忽略了《普甯藏》對該經的修訂。
又如《大正藏》依據《高麗藏》收入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但對卷一的第42號[2]《阿閦佛國經》到第115號《觀世音觀經》等74部經作校記如下:“校者曰:自《阿閦佛國經》至《觀世音觀經》與元、明兩本大異。故今以元本對校明本,別載卷末。”[3]並在卷一的卷末“以明本載之,以元本對校”[4]把這74部經典又羅列了一遍,作為異文別本。但仔細審查這些經典,可以發現實際情況如下:
《麗藏》第42號至第61號經,等於明本第96號至115號經;
《麗藏》第62號經至98號經,等於明本第59號至95號經;
《麗藏》第99號經至115號經,等於明本第42號經至58號經。
兩者的著錄內容完全相同。也就是說,這兩者根本不是什麼“大異”,只是排序有差異而已。根據《眾經目錄》依照卷數多少先後排序的原則,可以肯定《麗藏》的次序是正確的,而明本的次序是錯誤的。產生錯誤的原因,可能是錯版所致。一般來說,校勘時遇到這種情況,只需在校記中加以說明即可,不需重出。
還有,初印本第14卷中的《佛說分別經》與第17卷中的竺法護譯《佛說分別經》重出。這個問題後來被發現,在六十年代的重印本中作了修訂,代之以乞伏秦法堅譯的《佛說阿難分別經》。
第二、著譯者的勘正問題
漢文大藏經中有不少原來失譯者名的經本,或原來缺本而後來尋訪發現的經本。對於這些經本,後代經錄往往有因考訂不當而誤題著譯者姓名的。對於一部嚴謹的新編大藏經來說,應該對這些著譯者加以慎重的考訂,以免謬種流傳。但《大正藏》對這個問題幾乎不加考慮,基本沿襲原來的著錄。這樣一來,自然也削弱了《大正新修大藏經著譯目錄》的學術價值。呂澄先生在《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譯本部分的編次》[5]對這個問題有所敘述,在其《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6]中對不少經典的著譯者的勘正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為避文繁,在此不一一羅列,讀者可以對照參看。
第三、校勘疏漏問題
總的來說,《大正藏》的校勘品質是比較高的,但仍然存在不少漏校、錯校之處。包括對排字錯誤的漏校。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大正藏》遠不能說是一個權威的、標準的版本。當然,如前所述,“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我國的二十四史集中了全國的一流學者,費時多年進行校對標點,但仍有不少不能盡如人意的錯誤。近年以來筆者一直從事佛教典籍的校勘標點等工作,深知其中的甘苦。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對《大正藏》的校勘疏漏提出批評。當然,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象佛典校勘這樣難度極高的工作,是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我相信,經過一代又一代學者的艱苦努力,這個問題最終一定能夠得到圓滿解決。
五、錯版及擅加文字問題
十多年前,筆者在研究《那先比丘經》時,意外地發現《大正藏》所收的二卷本《那先比丘經》竟然出現一處實在不應該有的錯版及擅加文字問題。這個問題雖然也可以歸入上述第四項校勘問題中,但因為敘述起來比較複雜,故此單列一條。
該二卷本《那先比丘經》在《大正藏》中編為第1670號,載第32卷。其中第702頁中第27行末至702頁下第9行有一段關於智者與愚者作惡後得殃是否相同的問答。為了說明問題起見,我把三卷本《那先比丘經》的同一段問答[7]也抄錄如下,以作比較。
二卷本
王複問那先:“智者作惡,愚人作惡,此兩人殃咎,誰得多者?”那先言:“愚人作惡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王言不知那先言。王言:“我國治法,大臣有過則罪之重,小民有過罪之□[8]。是故我知智者作過惡得殃大,愚者作惡得殃小。”那先問王:“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為燒鐵,一人不知。兩人俱前取燒鐵。誰爛手大者耶?”王言:“不知者手爛。不制其身口者,不能持經戒,如此曹人亦不樂其身。”那先言:“其學道人者,能制其身,能制口,能持經戒。能一其心得四禪,便能不復喘息耳。”王言:“善哉!善哉!”
三卷本
王複問那先:“智者作惡,愚人作惡,此兩人殃咎,誰得多者?”那先言:“愚人作惡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王言不如那先言。王言:“我國治法,大臣有過則罪之重,愚民有過則罪之輕。是故智者作惡得殃大,愚者作惡得殃小。”那先問王:“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為燒鐵,一人不知。兩人俱前取燒鐵。誰爛手大者耶?”王言:“不知者爛手大。”那先言:“愚者作惡,不能自悔,故其殃大。智者作惡,知不當所為,日自悔過,故其殃少。”王言:“善哉!”
上述兩段文字,前半部分相同,後面劃線的部分大異。很顯然,三卷本的文字正確,二卷本的文字錯誤。對照巴厘語《彌蘭陀王之問》,結論也完全一樣。在此再將巴厘語《彌蘭陀王之問》的相關段落翻譯如下[9]:
王問:“那伽先那尊者!知者行惡與不知者行惡,誰的禍大?”
長老回答:“大王!不知者行惡,所得禍大。”
“原來如此。尊者那伽先那!我們的王子、大官如果作惡,要比不知者作惡,予以加倍的處罰。”
“大王!您(對下述情況)是怎麼想的呢?如果有一個灼熱、燃燒著的鐵球。一個人知道而去握它;另一個人不知道也去握它。那麼,誰被燒傷得厲害呢?”
“尊者!不知道而去握它的人被燒傷得厲害。”
“大王!與此相同,不知者行惡,所得禍大。”
“善哉!尊者那伽先那!”
那麼,二卷本有無上述三卷本錄文中劃線的“大。那先言:愚者作惡,不能自悔,故其殃大。智者作惡,知不當所為,日自悔過,故其殃少。王言:善哉!”這一段話呢?有!就在702頁下第25行至第27行。全文一字不差,只是最後一句彌蘭陀王的讚歎語中多說了一個“善哉”而已。進而仔細檢查,發現從二卷本702頁下第6行“不制其身口者”起,到同欄第24—25行“和所為得人者”止的295個字都與原文不相吻合,肯定是從其他地方脫落後竄入此處的。
那麼,這295個字是從哪裡脫落的呢?仔細研究,這295個字包括了四個問題:關於止息喘息的問答的後部分;關於大海的問答;關於得道思維深奧眾事的問答;關於人神、智、自然異同問答的前部分。經查,原來它們應該位於第703頁上欄第16行的“不能”與“那先問王”之間。“不能”以前,正是關於止息喘息問答的前部分;而“那先問王”以後,正是關於人神、智、自然異同問答的後部分。二卷本此處本來語義也不通。但把脫落的文字加入後,意義就連貫通順了。與三卷本的相同部分也正好吻合。
但新的問題又出來了。為了便於說明這個問題,在此還是把將脫落文字插回原處之後二卷本的有關段落與三卷本的有關段落抄錄比較如下:
二卷本
王複問那先:“卿曹諸沙門說言:‘我能斷喘息之事。’”王言:“奈何可斷喘息氣耶?”那先問王:“甯曾聞志不?”王言:“我聞之。”那先言:“王以為志在人身中耶?”王言:“我以為志在人身中。”那先言:“王以為愚人不能不制其身口者,不能持經戒,如此曹人亦不樂其身。”那先言:“其學道人者,能制其身,能制口,能持經戒。能一其心得四禪,便能不復喘息耳。”王言:“善哉!善哉!”
三卷本
王複問那先:“卿曹諸沙門說言:‘我能斷喘息之事。’”王言:“奈何可斷喘息氣耶?”那先問王:“甯曾聞志不?”王言:“我聞之。”那先言:“王以為志在人身中耶?”王言:“我以為志在人身中。”那先言:“王以為愚人不能制其身口者,不能持經戒者,如此曹人亦不樂其身。”那先言:“其學道人,能制身口,能持經戒。能一其心,得四禪,便能不復喘息耳。”王言:“善哉!”
上述二卷本錄文中的劃線部分為移入的脫落文字。與三卷本錄文對照,最大的差別在於三卷本說:“愚人不能制其身口”;而二卷本的文字卻是“愚人不能不制其身口”,多了一個“不”字,以致文意完全相反。很顯然,三卷本的文字是正確的。證之巴厘語《彌蘭陀王之問》,結論也相同。
我起先以為上述文字的錯亂乃至那個多出的“不”字都是由於原底本《高麗藏》錯版造成的。因為《高麗藏》一版23行,行14字,每版322字。如果有幾個段落不滿行,就只有300字左右,與前述295字大體吻合。也就是說,很可能是由於《高麗藏》發生錯版,從而導致《大正藏》文字的錯亂。可是在對勘了《高麗藏》以後,發現《大正藏》的這一段文字,即前述702頁下第6行“不制其身口者”起,到同欄第24—25行“和所為得人者”止的295個字,如果把其中成問題的那個“不”字取掉,則剩下的294字恰好就是《高麗藏》中《那先比丘經》下卷的第19版。但《高麗藏》版序正確,絲毫沒有錯版問題。而《大正藏》所以發生錯亂,是由於把該第19版的文字搬到第18版之前的緣故。
現在事情就清楚了,問題的確如我判斷是錯版所致。但不是《高麗藏》錯版,而是《大正藏》錯版。或者由於《大正藏》所利用的那部《高麗藏》的印本此處裝裱顛倒所致?但《高麗藏》每版均有版片號,按道理能夠發現這種顛倒。不管怎樣,錯版發生了,但沒有被發現糾正。不僅如此,《大正藏》的校對者竟然擅自又加上一個“不”字。從上下文可知,由於《大正藏》的校對者在錄校該經時,沒有發現此處文字錯亂。所以在原文照錄,抄錄到錯亂處,即“王言:‘不知者手爛。制其身口者,不能持經戒,如此曹人亦不樂其身[10]’”這一段話時,發現它的意思與佛教義理顯然有違。為了使文意能夠通順,便擅自在“制”前加上一個“不”字。從而將原脫落的294個字增加為295個字。
按照《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對該二卷本《那先比丘經》,《大正藏》曾用正倉院聖語藏本及巴厘語本作了對校。聖語藏本的情況如何,筆者未見原件,不能發表意見。如前所引,巴厘語《彌蘭陀王之問》的該節文字十分清楚;此外,三卷本的文字也十分清楚,完全可以參照。不知何以竟沒有引起校對者的注意。另外,《大正藏》並沒有理校的體例,所以不應出現理校。即使理校,按規矩應該出校記說明。而校對者對自己加的這個“不”字竟不置一詞,應該說是很不嚴肅、很不負責任的。遺憾是六十年代修訂時也沒有發現這個錯誤,以致留存至今。我真誠地希望類似的錯誤在《大正藏》中僅此一例。
總之,《大正藏》固然在五十餘年中獨擅勝場,但它存在的種種嚴重問題使得它與盛名難副。問題還在於佛典整理比較專門,使得《大正藏》易於用它的盛名來掩蓋它的問題,從而誤導讀者與研究者。因此,對於佛教文獻工作者來說,編纂一部真正可靠、實用的大藏經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同志仍須加緊努力。
當今,與人們用大文化的觀念重新審視佛教相適應,新的編輯大藏經的熱潮也在出現,已經編輯與正在編輯的大藏經已有好幾部。遺憾的是,大家各自為政,各行其是。這種局面的優點是百花齊放,缺點是水準參差不齊。再就是重複勞動,造成人力、物力的嚴重浪費。世界正在縮小,交流正在擴大;時代正在前進,學術正在前進。那麼,有沒有可能順應這一趨勢,團結各界力量,總結前人經驗,發揮今日優勢,電腦版、書冊版並重,編纂出一部無愧於當今時代的新的精校標點漢文大藏經呢?
[0]參見拙作:《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載《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五期。
[1]《大正藏》,第八十五卷,第1192頁下。
[2]原目錄無序號,該序號系筆者依照原目錄順序所編,下同。
[3]《大正藏》,第55卷,第115頁。
[4]《大正藏》,第55卷。第122頁。
[5]《呂澄學術論著選集》,第三卷,齊魯書社,1991年7月,1621頁。
[6]《呂澄學術論著選集》,第三卷,齊魯書社,1991年7月,1644頁。
[7]《大正藏》,第32卷,第718頁上。
[8]原文此處空一字。
[9]據中村元、早島鏡正日譯本轉譯。見中村元、早島鏡正:《彌蘭陀王之問》,平凡社,1972年8月,第246頁。
[10]未劃線者為原《高麗藏》第17版文字的尾部,劃線者為竄入之原《高麗藏》第19版文字的首部。